论述新历史主义“文史合一”观的积极意义和理论缺陷
论述新历史主义“文史合一”观的积极意义和理论缺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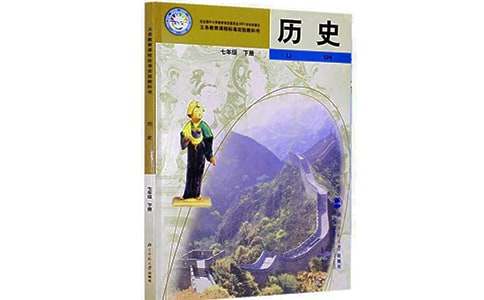
一、“文史合一”观的理论贡献
(一)更新了对文学和历史二者关系的认识
新历史主义的“文史合一”观,更新了我们原有的对文学和历史关系的认识,在传统历史主义看来,文学文本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对历史本身,即过去的事实的一种反映,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就代表了这种观点,他们将文学文本当成对客观的历史事实的摹写,摹写当然是追求客观真实的,文学作品如果能获得历史文本所具有的真实感,就是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因而,在历史中各种社会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文学作品得以产生并具有了自己的特性,传统的观点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具体的历史语境,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语境的一种反映,也就是说,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因而,尽管人们承认文学可以虚构,可以想象,包含有情感因素,但文学终究是一种历史现象,人们往往以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历史真实程度来评判文学作品价值的高低,在这里,历史具有绝对的权威,文学必须臣服于历史。但是,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并不具有高于文学的优越地位,历史由于其文本性和叙述性而向文学靠拢,历史和文学同属于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文学和历史并无明显的界限,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复杂的相互纠缠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在形式主义看来,文学文本是独立存在的,既然如此,有自身独立价值的文学文本为什么非要和历史、社会、文化纠缠不清呢?文学作品为什么非得受这些因素的制约呢?他们认为文学文本如果要独立,就必须摆脱这些因素的纠缠,这样文学研究才能回到文学的本体——文学文本上来,而联系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来研究文学的做法则是舍本逐末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文学文本为中心,而不必顾及其它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因而在形式主义者的文学研究中就割裂了文学和历史的联系,他们认为文学和历史是泾渭分明的两件事情,文学研究者应该将注意力放在文学文本上,同时在文学研究中放逐历史,文学的存在价值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性”,它无需靠历史来证明自己,文学作品是否具有历史蕴涵已经微不足道。文学的历史维度被放逐之后,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性质被形式主义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注重从语言学角度入手研究文本的文学性,即考察作者运用了什么样的语言手段,何种文学结构或文学技巧、表达方式及由此而产生的文本的文学性。
因而,无论是传统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决定文学的观点,还是形式主义认为历史和文学无关的看法,其实都是将文学和生活、文本与历史语境对立了起来,过分强调二者之间的对立性和差异性,这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思想的体现,而新历史主义所揭示给我们的却是一种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即文学和历史走向了同一,而不是走向对立,这种变化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这里不能不联系到20世纪文艺理论“语言论转向”的大背景来认识这个问题。语言,具体讲是文本仍然是新历史主义关注的中心,一切文化实践活动,其实都是一种语言活动,形式主义者注重认识文本的语言性质,而新历史主义的精神导师之一福柯和一般的形式主义者不同,他把文本置于话语活动中进行考察。在福柯看来,话语活动是一个动态的、流动的过程,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文本和语境等多种因素,而不仅仅局限于孤立的文本,通过对这多种因素的强调,尤其是引入了语境这样一个概念之后,文本不再是孤立存在的了,而是指向了具体的社会历史,因为语境代表了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而任何话语活动都是在一定的语境之中发生的。福柯还认为,话语始终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权力总是通过话语去运作,从而话语总是具体的、历史性的话语实践,植根在社会制度之中并受到其制约。新历史主义从中认识到:文本作为话语总是权力运行的场所,是历史现形的所在,因而文本具有历史性。
我们可以将新历史主义关于文学和历史的关系的观点概括如下:首先,历史和文学都是一种文本,都是一种语言活动,它们没有根本区别,谁也不能决定谁,这表明新历史主义确实受到了形式主义的影响;其次,作为话语活动中的文本又和语境等其它因素联系起来,文本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受到社会结构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因而文本具有历史性、功利性,文学并不是那种脱离历史语境的纯审美空间,这样新历史主义又和形式主义区别开来。新历史主义强调的不是历史和文学的那种决定和被决定、谁高谁低的关系,而是一种“互文性”关系,历史和文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纠缠在一起,新历史主义就这样更新了我们对文学和历史关系的认识。
(二)促进了我国新历史主义的小说创作
文学和历史走向同一,文学具有真实性,历史具有虚构性,文学再也不必象以前那种处处臣服历史,处处受历史的制约,这等于是在某种程度上解放了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使历史文学创作呈现出异乎寻常的景观,这种颇具新意的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传入我国之后,和我国的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相结合,大大促进了我国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
文学和历史相互开放之后,它们是一种“互文性”的关系,文学和历史作为文本彼此渗透,文学创作不必再对历史话语顶礼膜拜、小心翼翼、亦步亦趋,作家可以在历史的原野上自由驰骋,甚至可以通过叙述话语操纵和戏弄历史,不怕触犯历史的权威,历史从一个威严崇高的老人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历史虽然是“非叙述、非再现”的,但我们只有通过历史文本才能接触到历史,而历史文本是一种主体叙述的产物,也就是说新历史主义认为不存在客观的历史,只存在主体叙述的历史,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主体,对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对过去事件的客观再现,因而具有相当大的主体性、主观性,同一个历史碎片,体现在文本中可能会有各种差别很大,甚至完全对立的说法,正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在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看来,所谓的正史不过也就是一种文本,一种官方的说法而已,它只是众多说法中的一种,不再具有以前的那种权威性,在这种正史基础上形成的传统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已经程序化、模式化,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产生以后,历史小说创作就会由一种权威的声音变成众声喧哗,新历史主义的小说创作因而可以颠覆那种宏大叙事,把过去所谓单线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线小写的历史(histories),历史真实不能只通过某一部历史文本体现出来,而必须通过各种文本体现出来,而我们以前则只是单纯推崇官方正史,历史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已趋于僵化,因而他们通过对小历史和复数历史的书写来拆解和颠覆大历史,从而使宏大叙事不断微型化,小说创作也因此实现了一个转变,即“从民族寓言到家族寓言,从宏观到微观,从显性政治学到潜在存在论。”[34]新历史主义作家抛弃以文本形式存在的“正史”,而更加注重“野史”,“秘史”、“家史”、“族史”,在中国,“为尊者讳,为亲者隐”的治史传统根深蒂固,正史主要是为尊者、亲者歌功颂德,而野史、秘史、家史、族史等民间传统的历史故事则更有可能以其历史本来面貌存在和显现。